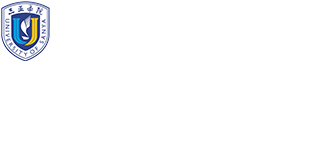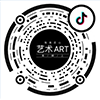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五指山市的夜色和黎明洗净了同学们之前的疲惫。早餐之后,考察组的同学们带着一份依恋离开了五指山市朝着东北方向的水满乡初保村进发。依然是崇山峻岭、依然是山道弯弯。不知不觉,眼前出现了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路边的树上结满了菠萝蜜,山涧的小溪边有一群孩子在嬉水抓鱼。如此的世外桃园使同学们一时忘情于山水之间。当村民用手给大家指向初保村的方位,同学们才意识到横亘在前方的是一个十分险峻的陡坡,这里离初保村还将有一段艰难的行程,而且是七弯八转的山间小路。
在村委会朱主任的引领下,司机将车小心冀冀地将车开进了山里,绕过一个山坳,一片完整的黎族船形屋终于呈现在眼前。初保村,号称海南第一黎村,这里居住着七十多户黎族家庭,村子背山朝阳,几十个被人们称为船形屋的茅草屋顺山势自下而上呈阶梯分布。村前是一片大水田,“牙合河”从村头流过,流水拍打着河床上的大石头,溅起清亮的水花。
递上一支烟,同学们跟老村长攀谈起来,村长姓王,少言寡语,夹着烟卷轻轻微笑地看着大家,间或点头或摇头。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常年与山的无语对峙,已经习惯了用沉默的方式来表述思想。只是当谈起过不了多久,因某位老板开发漂流探险旅游项目,这个村子的村民将全部搬迁到离这儿几里之外新建的商品房,而现有的船形屋将改造开发为旅游渡假村时,他凝视着对面山林中的重重雾霭,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表现出一种欲说还休的神情。
船形屋并非海南黎族聚落最初的居住方式,“有夷人,无城郭,殊异居……号曰黎,巢居深洞。”宋人乐史的记载说明黎族人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摇摆不定的树上居住的,而船形屋的形成应该是在秦汉时期,黎族先民作为百越的一支(称为驼越)大规模从两广一带迁徙至海南岛,他们带来了河姆渡文化中干栏式长屋的居住方式,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渐渐发展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船形屋式的黎族居住方式。船形屋外观和屋内的形制上都具有船的特征,屋前有类似于船台的小平台,屋后用藤条或木料结扎成半圆形的造型,颇似船的尾部。从这种外观像船的特点来看,似乎黎族民间流传的黎族先民是海上漂泊上岛的传说有一定的道理的。干栏式的船形屋前面离地面一至二米,后面则离地面的高度不到一米,在屋子下面形成楔形空间,这个空间用来养牛羊猪犬和堆放杂物。船形屋的结构及空间应用,凝聚了黎族人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属于古代遗存,因为船形屋的茅草和木质因为易于腐烂的原因都只能保持几年到十几年,但其建造形制是深植于黎族人民内心的根,也只有在船形屋这样的生存空间里的,黎族人才能感受到沉淀之中的民族文化,寻找到对现实生活的认同。
不得不离开初保村了,握着王老村长的手,无法想像,当他们住进钢筋水泥铸成的现代化的楼阁之时,灵魂还能否像现在这样安适?当现在的船形屋变成了旅游度假村之后,牙合河水拍打河床的声音,是否依然悦耳、动听……
天空中飘起了淅淅小雨,调研小组的同学们绕着五指山脉向北朝着琼中黎苗族自治县继续行进,渐渐地离开了山涧曲径,途经什运乡上了224国道,两边低矮的树丛整洁、有序,人工修剪的印迹明显,一路将我们引向了县政府的所在地——营根镇。
琼中有着绝好的地理环境,近山、临水、聚气……天色向晚的时分,远处的鹦歌岭、黎母山、五指山和吊罗山形成天然的屏风,细雨朦朦中云层低吟、山色厚重,近景是一大片水田,好一副田园暮色。然而,刚从五指山润泽绿色中走出来的同学们,总感到空气中弥漫着些许浮燥的气息,初保村的原野气质与这里浓重的旅游开发的商业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总感到内心的不适又说不出哪里不对。百花岭下的百花廊桥整个桥身用了最饱满鲜艳的中国红,无论如何,在视觉上无法都将一座通红的廊桥协调地嵌入一个以黎苗族聚居为民风的环境,突兀、乍崩的让人不知所措。离廊桥不远,有一处的低洼地带一直延伸至小河边,俯视下去,一片底屋黑瓦,同学们找到巷口,那里挂着一块牌子,写着“营根镇琼竹巷”,顺着巷口走下去,看见一些破损的老屋,陈旧的墙面上张贴着各种广告和鸦涂着各种标语。这里应该是城镇化进程中被遗漏的最后角落,与后面一排排的高楼大厚遥相矗立,依然是极不和谐。巷口的老树下,闲置着一把颇为现代的沙发。是谁,曾在这里怀想与歌吟?
一方是古巷深宅、一方是现代高楼,在过去与现代、古老与文明之间又间或掺杂如百花廊桥般看似汇集了黎苗文化风情的典型人工构筑物。难道,在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今天,如此做法真是贯穿过去与未来的通途吗?在方兴未艾的建设大潮中,如何对待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更新,文化的保护、挖掘和传承着实是一个耐人思考、深省的严峻命题!
当晚,同学们留宿在琼中。怀着思索,难以入眠……
(文/杨丹 图/黄凌 编辑/方超)